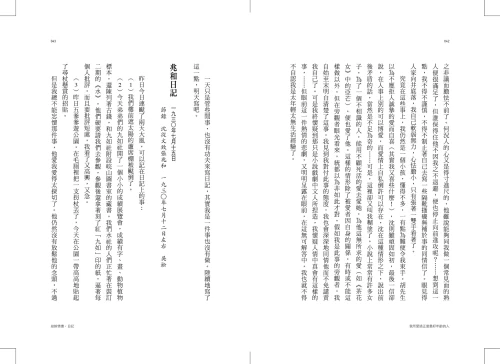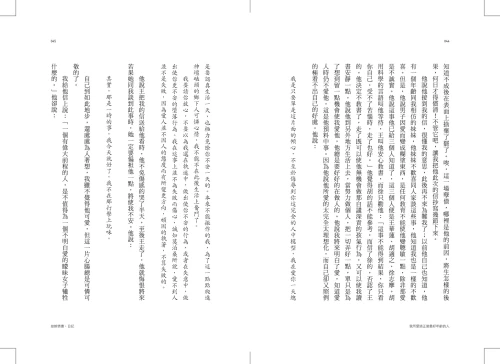我所愛過正當最好年齡的人:一九三○-一九六六年沈從文家書
商品編號:08030169
定價: 480 元
優惠價: 79折 379 元
優惠活動
內容簡介
諾貝爾文學獎最大遺珠沈從文的遺留家書
一探作家與妻子最刻苦銘心的愛戀
「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
歷經了六十多年,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仍然如此自問。
沈從文是近代中國最閃亮的作家,幼年時深受五四運動影響,觸發了他對文學的熱愛。他曾發表過多篇膾炙人口的小說,並於1988年一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最有機會獲獎的候選人,但他卻在同年不幸與世長辭。
1929年,沈從文受到胡適之邀,來到上海公學講學,他一眼就愛上了時年18歲的張兆和。當時還是學生的張兆和,曾在日記中喃喃自語「不懂得什麼叫愛」,並多次拒絕沈從文的追求。面對上海公學的才女佳人,沈從文以筆述情,寫了上百封情書,終於打動了張兆和的心。
才子佳人的結合,卻遭遇了大時代無情的變動,伴隨兩人共同看遍了民國初年的繁華盛事,也一起承受戰爭導致的紛亂與分離。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接踵而至的國共內戰,使得兩人體會如雲泥之差的生活。隨後,新中國的建立、參加下鄉土改,徹底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大時代的波浪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沈從文和張兆和兩人,在大時代下載浮載沉,用柴米油鹽來遮擋生活的刻苦辛酸。
張兆和是沈從文人生中最重要的存在,也是陪伴他不斷創作的友人。儘管沈從文的一生顛沛流離,甚至曾面對無情的政治批判而精神崩潰,但張兆和卻未從他身邊離去,甚至仍不斷鼓勵沈從文拿起筆來,寫下美麗動人的小說。沈從文家書從雙方踏入戀愛為起始,到文革前夕,收入了橫跨三十餘年的家書。頻繁的書信與細膩的情話,見證了兩人刻骨銘心的愛戀,也帶我們側看了大時代的演變。
--------------------------------------------------------------------------------------
內容摘句
「龐雜繁亂的人生中,無處不顯出它的矛盾衝突,如果沒有了這許多矛盾衝突,任人生如何龐雜,如何繁亂,各人在自己的軌道中,或與自己有關係的人中,走著他和平合拍的道路,世界雖大,便永遠是安靜的,沒有出軌的事情發生了。」──〈劫餘情書‧日記〉
「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種東西,並不比一株花更經得住年月風雨,用對自然傾心的眼,反觀人生,使我不能不覺得熱情的可珍,而看重人與人湊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湊巧是不會有的。」──〈劫餘情書‧日記〉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劫餘情書‧日記〉
「離你一遠,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邊來了。因為慢慢的靠近來的,是一種混同在記憶裡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別的。這才真是生命中最高的歡悅!」──〈霽清軒書簡〉
「我想喊一聲,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誰,原來那個我在什麼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筆,為什麼一下子會光彩全失,每個字都若凍結到紙上,完全失去相互間關係,失去意義?」──〈囈語狂言〉
作者介紹
沈從文、張兆和
沈從文
1902年出生於湘西鳳凰,他未滿15歲即擔任軍人,浪跡湘鄂川黔邊境地區,目睹血腥暴力的現實,又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而得到生活和人性的啟蒙。1923年秋前往北京,在北大旁聽,結識了徐志摩、郁達夫等文化俊英,開始發表充滿自敘傳色彩的作品。1928年南下上海,先後在上海中國公學、青島大學任教,創作漸趨成熟。1933年重返北京,並任天津「大公報」副刊主編。
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任教,內外交逼的孤獨感,使他展開對人生的抽象思辯,小說創作銳減。戰後回北大任教,同時主編報紙副刊。1949年中國政權更迭前後,他面臨無情的政治批判,導致精神崩潰,試圖結束自己生命未果。
1950年代以降,沈氏雖不忘情文學,但形格勢禁,乃將熱情投注於文物研究,並獲得輝煌成果,但他的文學業績則長期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1980年他曾短期訪美,1988年與世長辭。一生著作甚豐,代表作有《邊城》、《阿麗思中國遊記》、《月下小景》、《從文自傳》、《湘西散記》、《長河》、《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
張兆和
1910年出生於安徽合肥,於十姐弟中排行第三,童年在蘇州度過,並就讀父親所創辦的樂益女中;1932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文史系。翌年與沈從文結婚,長子龍朱、次子虎雛陸續出生,婚後有六年未外出工作。
抗戰期間在昆明教授中學英語。1954年起擔任《人民文學》雜誌編輯;1969年下放湖北五七幹校,1972年退休返回北京。1980年代初期,為重新輯印沈從文著作而做了大量篩選、審訂、校勘工作。筆名叔文、叔兆,曾出版由巴金編選的作品集《湖畔》。
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柯惠鈴
聯合推薦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彭小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須文蔚
歷史作家 謝金魚
作 家 蔡詩萍
作 家 張西
(依來函順序刊登)
沈從文與張兆和兩人以一種化外姿態,在不得不隨歷史與時代大浮大沉之下,體現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的知識分子修養,以「過生活」的常態來應對政治的詭祕變態。……回望上個世紀沈從文寫或不寫,提醒我們歷史的難測與傲然,而時代悲劇彌天蓋地,有誰能真正躲過?閱讀這批書信,使我們駐足凝思,也許歷史的幾年幾十年,不過是一瞬,但對於個人來說,它是獨有的、可貴的一世一生。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柯惠鈴
這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書信集,不僅收錄了沈從文追求張兆和的美好文字,也見證了他面對政治攻擊時的絕望與崩潰。更重要的是當沈從文無法跨越1949,他豐沛的故事與靈感淤塞在記憶中,本書如同一個時空膠囊,收錄了一個偉大文學心靈在亂世中和家人娓娓敘說的心事,尋常的一篇指導孩子寫作的信箋,都讓人感受到生命與時間巨大的重量。這本書雖然看似片斷與零散,真是一本讀也讀不盡的「大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須文蔚
我忘了什麼時候讀過這本書的,但幽幽淡淡,書香傳家的兩人書信,勾勒出了大時代的飄搖裡,人對愛與知識的堅定信念。至今讓我難忘。
──作家 蔡詩萍
目錄
導讀:人間熱淚已無多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柯惠鈴
劫餘情書‧日記
湘行書簡
飄零書簡
霽清軒書簡
囈語狂言
川行書簡
南行通信
跛者通信
破者的抒情
臨深履薄
後 記
試閱
由達園給張兆和 一九三一年六月 北平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
你們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我要玖到××來看看你,我說:「玖,你去為我看看××,等於我自己見到了她。去時高興-點,因為哥哥是以見到××為幸福的。」不知道玖來過沒有?玖大約秋天要到北平女子大學學音樂,我預備秋天到青島去。這兩個地方都不像上海,你們將來有機會時,很可以到各處去看看。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歷史上為保留下一些有意義極美麗的東西,物質生活極低,人極和平,春天各處可放風箏,夏天多花,秋天有雲,冬天颳風落雪,氣候使人嚴肅,同時也使人平靜。××畢了業若還要讀幾年書,倒是來北平讀書好。
你的戲不知已演過了沒有?北平倒好,許多大教授也演戲,還有從女大畢業的,到各處台上去唱崑曲,也不為人笑話。使戲子身分提高,北平是和上海稍稍不同的。
聽說××到過你們學校演講,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我是同她頂熟的一個人,我想她也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紅臉不會有再好的印象留給學生。這真是無辦法的,我即或寫了一百本書,把世界上一切人的言語都能寫到文章上去,寫得極其生動,也不會作一次體面的講話。說話一定有什麼天才,×××是大家明白的一個人,說話嗓子洪亮,使人傾倒,不管他說的是什麼空話廢話,天才還是存在的。
我給你那本書,《××》同《丈夫》都是我自己歡喜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個最好的記憶,因爲那時我正在吳淞,因愛你到要發狂的情形下,一面給你寫信,一面卻在苦惱中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我照例是這樣子,做得出很傻的事,也寫得出很多的文章,一面糊塗處到使別人生氣,一面清明處,卻似乎比平時更適宜於做我自己的事。××,這時我來同你說這個,是當一個故事說到的,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難受。這是過去的事情,這些過去的事,等於我們那些死亡了最好的朋友,值得保留在記憶裏,雖想到這些,使人也仍然十分惆悵,可是那已經成爲過去了。這些隨了歲月而消失的東西,都不能再在同樣情形下再現了的,所以說,現在只有那一篇文章,代替我保留到一些生活的意義。這文章得到許多好評,我反而十分難過,任什麼人皆不知道我爲了什麼原因,寫出一篇這樣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出現。
我近日來看到過一篇文章,說到似乎下面的話:「每人都有一種奴隸的德性,故世界上才有首領這東西出現,給人尊敬崇拜。因這奴隸的德性,爲每一人不可少的東西,所以不崇拜首領的人,也總得選擇一種機會低頭到另一種事上去。」××,我在你面前,這德性也顯然存在的。爲了尊敬你,使我看輕了我自己一切事業。我先是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無用,所以還只想自己應當有用一點。到後看到那篇文章才明白,這奴隸的德性,原來是先天的。我們若都相信崇拜首領是一種人類自然行爲,便不會再覺得崇拜女子有什麼稀奇難懂了。
你注意一下,不要讓我這個話又傷害到你的心情,因為我不是在窘你做什麼你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只在告訴你,一個愛你的人,如何不能忘你的理由。我希望說到這些時,我們都能夠快樂一點,如同讀一本書一樣,彷彿與當前的你我都沒有多少關係,卻同時是一本很好的書。
我還要說,你那個奴隸,為了他自己,為了別人起見,也努力想脫離羈絆過。當然這事做不到,因為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覺得負疚,我以為很不好。我曾做過可笑的努力,極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別人崇拜我願意做我的奴隸時,我才明白,我不是一個首領,用不著別的女人用奴隸的心來服侍我,卻願意自己做奴隸,獻上自己的心,給我所愛的人。我說我很頑固的愛你,這種話到現在還不能用別的話來代替,就因為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後許可我做我要做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說什麼時,你都能當我是一個比較愚蠢還並不討厭的人,讓我有一種機會,說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話,這點點是你容易辦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說到「我愛你」時你就覺得受窘,你也不用說「我偏不愛你」,作為抗拒別人對你的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實上卻毫無用處的。有些人對成日成夜說:「我讚美你,上帝!」有些人又成日成夜對人世的皇帝說:「我讚美你,有權力的人!」你聽到被稱讚的「天」同「皇帝」,以及常常被稱讚的日頭同月亮,好的花,精緻的藝術回答說「我偏不讚美你」的話沒有?-切可稱讚的,使人傾心的,都像天生就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他們管領一切,統治一切,都看得極其自然,毫不勉強。一個好人當然也就有權力使人傾倒,使人移易哀樂,變更性情,而自己卻生存到一個高高的王座上,不必做任何聲明。凡是能用自己各方面的美攫住別的人靈魂的,他就有無限威權,處置這些東西,他可以永遠沈默,日頭,雲,花,這些例舉不勝舉。除了一隻鶯,他被人崇拜處,原是他的歌曲,不應當啞口外,其餘被稱讚的,大都是沈默的。××,你並不是一隻鶯。一個皇帝,吃任何闊氣東西他都覺得不夠,總得臣子恭維,用恭維作爲營養,他才適意,因爲恭維不甚得體,所以他有時還發氣駡人,讓人充軍流血。××,你不會像皇帝。一個月亮可不是這樣的,一個月亮不拘聽到任何人讚美,不拘這讚美如何不得體,如何不恰當,它不拒絕這些從心中湧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聽一個並不十分聰明的人,用各樣聲音,各樣言語,向你說出各樣的感想,而這感想卻因爲你的存在,如一個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裏而起的,你不覺得這也是生存裏一件有趣味的事嗎?
「人生」原是一個寬泛的題目,但這上面說到的,也就是人生。
為帝王作頌的人,他用口舌「娛樂」到帝王,同時他也就「希望」到帝王。為月亮寫詩的人,他從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裏,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東西了。他是在感謝情形中而說話的,他感謝他能在某一時望到藍天滿月的一輪。××,我看你同月亮一樣。是的,我感謝我的幸運,仍常常爲憂愁扼著,常常有苦惱(我想到這個時,我不能説我寫這個信時還快樂)。因爲一年內我們可以看過無數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們頭上的,還是那個月亮。這個無私的月不單是各處皆照到,並且從我們很小到老還是同樣照到的。至於你,「人事」的雲翳,卻阻攔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個白日帶走了一點青春,日子雖不能毀壞我印象裏你所給我的光明,卻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個女子在詩人的詩中,永遠不會老去,但詩人,他自己卻老去了。」我想到這些,我十分憂鬱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種東西,並不比一株花更經得住年月風雨,用對自然傾心的眼,反觀人生,使我不能不覺得熱情的可珍,而看重人與人湊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湊巧是不會有的。我生平只看過一回滿月。我也安慰自己過,我説:「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我應當爲自己慶幸,……」這樣安慰到自己也還是毫無用處,爲「人生的飄忽」這類感覺,我不能夠忍受這件事來強作歡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憶裏光明全圓,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著負疚的,因爲並不是由於你愛不愛我。
彷彿有些方面是一個透明了人事的我,反而時時為這人生現象所苦,這無辦法處,也是使我只想說明卻反而窘了你的理由。
××,我希望這個信不是窘你的信。我把你當成我的神,敬重你,同時也要在一些方便上,訴說到即或是真神也很糊塗的心情,你高興,你注意聽一下,不高興,不要那麼注意吧。天下原有許多稀奇事情,我××××十年,都缺少能力解釋到它,也不能用任何方法說明,譬如想到所愛的一個人的時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許多,全身就發熱作寒,聽到旁人提到這人的名字,就似乎又十分害怕,又十分快樂。究竟為什麼原因,任何書上提到的都說不清楚,然而任何書上也總時常提到。「愛」解作一種病的名稱,是一個法國心理學者的發明,那病的現象,大致就是上述所及的。
你是還沒有害過這種病的人,所以你不知道它如何厲害。有些人永遠不害這種病,正如有些人永遠不患麻疹傷寒,所以還不大相信傷寒病使人發狂的事情。××,你能不害這種病,同時不理解別人這種病,也真是一種幸福。因為這病是與童心成為仇敵的,我願意你是一個小孩子,真不必明白這些事。不過你卻可以明白另一個愛你而害著這難受的病的痛苦的人,在任何情形下,卻總想不到是要窘你的。我現在,並且也沒有什麼痛苦了,我很安靜,我似乎為愛你而活著的,故只想怎麼樣好好的來生活。假使當真時間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時或者還是眼前一樣,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學的一個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許多小孩子的母親,我們見到時,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個作品上,以及任何一個世界名作作者的傳記上,最動人的一章,總是那人與人糾紛藤葛的一章。許多詩是專為這點熱情的指使而寫出的,許多動人的詩,所寫的就是這些事,我們能欣賞那些東西,為那些東西而感動,卻照例輕視到自己,以及別人因受自己所影響而發生傳奇的行為,這個事好像不大公平。因為這個理由,天將不許你長是小孩子。「自然」使蘋果由青而黃,也一定使你在適當的時間裏,轉成一個「大人」。××,到你覺得你已經不是小孩子,願意做大人時,我倒極希望知道你那時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有些什麼感想。「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推的,我的生命等於「萑葦」,愛你的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裡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爲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氣,許我在夢裡,用嘴吻你的腳,我的自卑處,是覺得如一個奴隸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腳,也近於十分褻瀆了你的。
我念到我自己所寫到「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時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葦,一生中,每當一次風吹過時,皆低下頭去,然而風過後,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遠折伏,永遠不再做立起的希望。
一九三一年六月
推薦序文
人間熱淚已無多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經歷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乃至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權輪替與社會大變動。浩浩蕩蕩的歷史並不隨風流逝,崢嶸歲月也並非與光同塵,無論承平、戰亂還是動盪,知識分子以各種不同的文字書寫方式,敘明心跡,表達情感,抒發不平,甚至泣血吶喊,為時代留下見證,為歷史保存魂魄。在知識分子各式各樣文字書寫類型中,書信是極其珍貴難得的素材,原因是戰火、流離、政治清洗等等,往往使得不能成編的書信遺失散佚,又或是為了躲避周密文網,只好把敏感文字付之一炬。外在環境既不利書信存留,幸運留存的書信,還可能因為書信往返的兩方或他方,僅視這種文字書寫的方式,主要目的是溝通日常生活訊息,是以通篇請安問候外,多數內容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以及氣候、景色描述,少有透露書寫者內心世界、精神狀態、情感流動、歡笑淚水、激情落寞、熱鬧枯寂等,那麼這樣的書信對於理解知識分子在歷史風雲變幻中的命運,他們的抉擇,他們的挑戰、批判、卑微、俯就、磨難、狼狽等等,就不免牽強附會,不知所以了。
從各方面來看,沈從文的家書彌足珍貴。首先,數量相當可觀的沈氏家族書信並未在戰亂烽火、政治鬥爭中燬於一旦,儘管遺失許多,但保留下來的部分,時間跨度由上世紀三○年代至六○、七○年代,長達近四十年,對於觀察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較長時間中,其所經歷的複雜變化,能夠有較明晰的掌握。再者,書信來往以沈從文為中心,絕大部分的收信對象是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張兆和家世顯赫,她是民國初期少數擁有大學學歷的女知識分子,本身也從事文學創作,才華洋溢,且擅辭藻。家書中包含許多張兆和的覆信與去信,情真意切,諄諄叮囑,可貴的是她對生活永遠有一份樂觀以及拒絕苦難的情態。
回顧沈、張兩人從一九三○年代相識、相戀、步入婚姻,婚後組成小家庭,生活安適寧謐,兩人育有二子,平靜生活不幸被戰爭打亂。抗日炮火自北平打響,沈從文與友人為避戰禍,倉促離北平,先抵長沙,後再輾轉入昆明,張兆和則留在危城中,謢幼扶老,主持一切,直至一九三八年年底也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攜帶兩個幼子奔赴西南,一家人得以團聚。儘管沈從文家書中,戰時書信缺漏較多,惟殘餘的文字仍能鋪陳出中國知識分子戰前、戰時,判若雲泥的生活。戰爭帶來巨大的苦難,從沈從文與張兆和夫妻兩人最初鴻雁東西,乃至遷延數月對於張兆和到底要走還是要留,陷於反覆爭執的無奈,已可略窺端倪。當然,戰爭中知識分子所受折損,精神加物質實難數計,書信透露沈從文倉皇出逃,捨去一大批原視之如命的珍藏版圖書、字畫、古董、文物等,曾經有過的風華,落得人去樓空,傾筐倒篋。
戰爭的苦難未已,更大的災禍旋踵而至,知識分子感嘆著哀莫大於心不死。抗戰結束後,沈從文全家隨北大遷返北平,他與眾多相知相熟舊友,一度寓居北平城郊的西山,自然風光與友朋聚談,暫得難有的愜意平靜生活。豈料不數月,國共交戰,平津易手,華北「解放」,中共新政權登場,此後便是「虎踞龍盤今勝昔」的動盪歲月。社會主義革命掀起如火如荼的激情,一時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樣的革命歌典到處傳唱,而革命文章、革命故事、革命小說、革命文藝四方流傳,文學成了鬥爭的先鋒,成為改造社會的手段。
一九五○年代始,在新社會理應造「新人」的革命指引下,黨中央祭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政治口號,為中共建政拉開序幕,為了迎頭趕上「革命形勢」,人人爭先上綱上線,深揭猛批,檢討自身做人做事態度與群眾關係,更有甚者,不少人表現出痛心疾首、慚愧自責、涕泗橫流的感天動地狀,所有一切都代表著新時代降臨,舊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革命的烈火很快燒到知識分子,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宣布「思想改造」,目的是「清理知識分子隊伍」,如何清理並未有明確的指示,是以出身舊社會與西化、現代化沾邊的知識分子,個個惶恐畏懼,為求政治過關,不少人向黨獻心獻身,主動要求參加土改工作,他及她們到基層、到農村,向貧下中農學習,經風雨見世面,進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一波波的政治風暴在沈從文的書信中依稀可辨,只不過,書信中以間接而又隱晦方式描述現實,同時幾乎不曾正面提及政治運動,但沈從文發信的時間、地點,他走向工農的變化足跡與心路歷程,仍然呼之欲出。一九五○年代後,知識分子離城市「上山」與「下鄉」,與民國棄鄉就城,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社會意識形態,而社會主義政權講階段鬥爭、重視農村,對於向來沈浸於城市現代化文明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疑是當頭棒喝,如冷水澆背。
一九五○年代後,革命風暴從未止歇,只有勢如破竹再勢如破竹,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永遠沸騰著,永遠悲壯著。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三反」、「五反」,一九五五年批鬥「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一九五八年「反右」、「三面紅旗」,一九六四年「四清」及「大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革命浪頭一次比一次高,革命激情烈火熊熊,刺刀見血。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出身舊社會、受西方式教育、渾身沾染城市現代氣息的知識分子,隨時可能被指認是「反革命」分子,又或是修反派、黑幫分子,乃至牛鬼蛇神,在推陳出新的革命清洗中,只能說他們的命運如風中殘燭,朝不保夕。這段鬼哭狼嚎的日子,多少人身處政治風暴當下,萬念俱灰,不甘受辱與折磨,毅然走上絕路。另外一些拚了命活下來的,空有一身文史專才,傲人學歷,曠古才華,卻毫無用武之地。他們從勞心者變勞力者,蹲牛棚者有之,下放生產隊加入勞動生產者有之,所有一切都亂了套,執筆者不過就「識幾個狗字兒」,於是大部分的人不再寫、不能寫、不敢寫,而就算寫了也面不了世,如此而成了集體噤聲了。知識分子身陷牢籠,稱之文化浩劫當不為過。
歷史的偉岸、殘酷,令人生畏,惟事過境遷後,仍有餘意留人間。沈從文的家書,從另一側面透露出令人玩味旳訊息,即身處政治狂浪襲捲下,一種守著日常生活角落的不折不撓,如何成為個人躲過天下大亂、四分五裂的避風之所。換言之,沈從文與張兆和兩人以一種化外姿態,在不得不隨歷史與時代大浮大沉之下,體現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的知識分子修養,以「過生活」的常態來應對政治的詭祕變態。要言之,本書所收的最後幾封信,多出自於張兆和之手,當時她已下放到北京郊區的順義生產大隊,得空便寫信給身居北京的沈從文。這些書信中,張兆和提到著名的政治風頭浪尖上的「焦裕祿」革命烈士樣版,還有蘊釀著一場牽連甚廣的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已現苗頭,以及「四清運動」等等事件。談論這些動輒幾千幾萬人喊打喊殺的政治事件,已打入另冊的張兆和,書信中竟沒有流露一絲一毫議論,她的用語與寫家長里短之事,別無兩樣。一九六○年代,下鄉接受勞動改造的張兆和,已看不到過去書家世家出身的官、暮、驕、嬌、怨「五氣」,她完全習染抄襲自革命老區的種種作風,如稱呼他人通常在其姓氏上加「老」及「小」字,書信中張兆和不無自在地說著別人喊她叫「老張」,已然是兩世為人。舊與新,相去何其之遠之大?福禍順逆,相隔如薄紙,怎不叫人欷歔嘆息?
一九三○年代,自稱是「鄉下人」的沈從文,從鳳凰小城出走,他當過兵,做過許多卑賤工作,二十歲決意棄武從文,脫掉兵衣,隻身赴北京闖蕩。對一個無背景、無家世、無財力的青年來說,城市生活意味著連串挫折磨難。為了謀生,沈從文只能靠著一隻筆,不眠不休地寫。終於,沈從文的文章陸續見報,他漸漸受到名家矚目,各方逐漸對這個貧無以立錐之地的文壇新秀伸以援手,此後,沈從文的創作,不論題材、數量、風格乃至類型,都日益蜚聲於眾,他在文壇上已然屹立不搖。知名度提高後,交往圈自然隨之擴展。最早賞識沈從文文采的是郁達夫,兩人自然成為莫逆。再由郁達夫引介,沈從文與《語絲》作者群,包括徐志摩、梁實秋、周作人、朱光潛等人也過從甚密。徐志摩又把沈從文帶進《現代評論》圈子,由此而認識丁西林、陳源乃至吳宓。這些名單上的文人、學者,多半留學英、美,他們服膺理想浪漫主義,推崇唯情觀,沈從文身與其中,其文學作品的抒情色彩濃郁,自是有跡可尋。另一方面,在北平窮困無告的日子裡,沈從文與初闖文壇的胡也頻、丁玲夫婦相交甚篤,爾後在北大自由旁聽,更認識許多左傾的同鄉大學生,沈從文當時也接觸左翼文學,也知道共產革命、階級鬥爭理論,最終他卻並未與左翼有更深的來往。
現在看來,這位自稱「鄉下人」的唯美唯情作家,顯然並不「鄉下」,他筆下的湘西,和一九五○年代毛思想重農主義所提到的農村,相距豈可以道里計。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九三○年代與沈從文往還密切的英美派或是新月派,他們的文學理想與革命聲調南轅北轍,根本不符「鬥爭」需求。一九五○年代後,大多數唯美派封筆也屬必然,而沈從文這位被西方稱譽為中國最偉大的少數作家之一,在長達四、五十年的歲月中,名字便只能被煙沒,作品只能被塵封,浸淫浪漫、理想主義的他、一時間當然寫不出「革命文學」,於是他全心意投入「雜學」。約有十年時間,沈從文一頭鑽進中國工藝物品及服飾研究中,後者在幾年專心致志的努力下,也算小有所成。一九八○年代,政治復歸平靜,但人已老,筆已鈍,年華已逝,想重拾創作,豈非空中樓閣,水中泡沫?平靜沒有幾年,一九八吧年沈從文壽命來到終點,一切皆成往事。
回望上個世紀沈從文寫或不寫,提醒我們歷史的難測與傲然,而時代悲劇彌天蓋地,有誰能真正躲過?閱讀這批書信,使我們駐足凝思,也許歷史的幾年幾十年,不過是一瞬,但對於個人來說,它是獨有的、可貴的一世一生。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柯惠鈴
NT$379
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