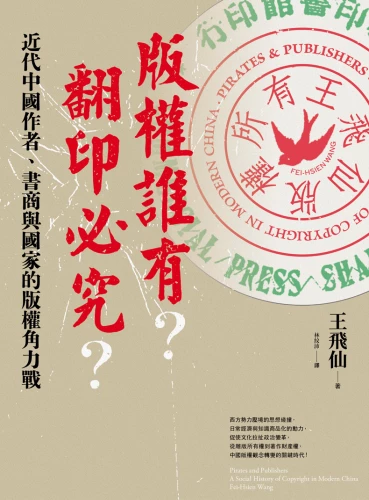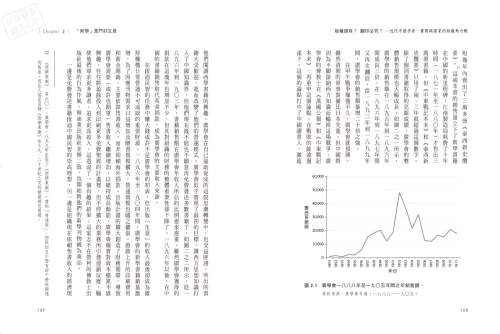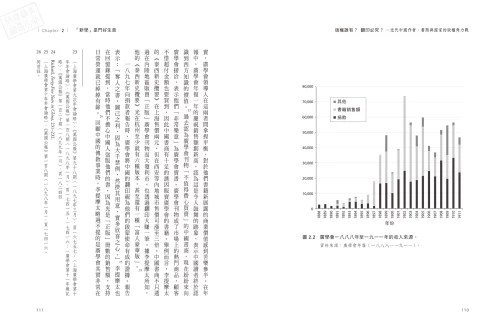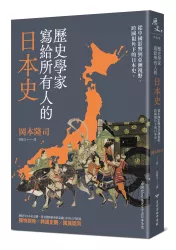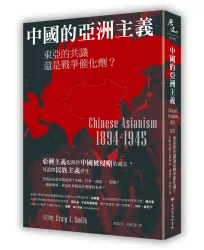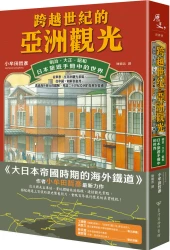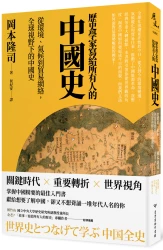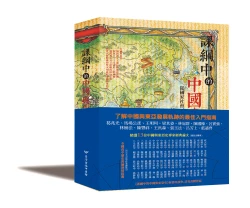內容簡介
第一部以版權為中心的近代中國社會史
爬梳零碎史料 揭露晚清至民初的作者、出版商如何抵制盜版
一場西方勢力壓境的思想碰撞,從雕版所有權到著作財產權,
中國版權觀念轉變的關鍵時代!
1903年商務印書館與嚴復簽訂第一份有系統的版權合約
智慧財產權散播中國
清末民初西學東漸,人們對新知的渴求,令西學書籍熱銷,書商、印刷商都想分杯羹,巨大的商業潛力令各式版本一時間湧入市面,更分不清正式版權歸屬哪方。當時的作者受西方版權概念啟發,覺醒到自己腦力勞動的成果正被瓜分,而自身並未獲益,生活無以為繼,開始想方設法捍衛權利。
「利潤」促使書商與作者團結起來,為版權正名發聲,近代中國的版權正義由此開展。
設圈套抵制盜版,上書呈維護出版!
書商督促政府立法、號召成立公會,甚至僱用偵探偵緝盜版。在缺乏有力的法律之時,建立起規範與秩序,藉此保護書籍,從而改變了中國對版權的概念。
王飛仙教授大量挖掘檔案史料,揭露版權觀念如何吸收中國的思想與習慣,在帝國晚期過渡為現代國家之際,以開創的精神不斷試探,並提到中共建國後,版權觀念又出現如何變革。本書從1890~1950年各界對版權的理解與實踐面向切入,探索文化產業、知識體系與法律規章在中國的大轉變。
本書特色:
1. 從現代中國社會史拉出版權史、著作權史,就晚清至1950年代著墨,看中國在版權方面如何從中掙扎、轉變到成長,一步步走到今日。借鏡他人同時可反思臺灣本身的版權史及現況。
2. 看到中國與西方對版權所有全然不同的概念。西方保障的是作者精神與智慧的「創作」;而中國則認為是擁有書籍的印刷刻版以及文稿的人。
3. 透過報紙廣告、書籍的權頁、版權憑摺、學部官報、盜版書等非傳統法律史的研究史料,以這些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碰到的物品,幫助讀者更容易了解版權。
作者介紹
王飛仙
王飛仙(Fei-Hsien Wang),歷史學家,政治大學碩士、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博士。現任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歷史系副教授,同時也是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age)副研究員。
研究領域為十九世紀下半二十世紀初期東亞的出版業,過去曾研究商務印書館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互動,出版專書為《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
譯者簡介
林紋沛
林紋沛,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歷史學系碩士。著有《行旅致知:李仙得、達飛聲等西方人建構的台灣知識(1860–1905)》、《跨越世紀的信號2:日記裡的台灣史(17–20 世紀)》(合著)。現為專職譯者,喜歡翻譯時的靈光乍現,譯著有《論友誼》、《從彼山到此山》、《家園何處是》、《強鄰在側》等。
名人推薦
2020年美國法律史學會彼得.斯坦因(Peter Gonville Stein)最佳著作獎
著述、閱讀和出版歷史學會(SHARP)「德隆書籍史圖書獎」亞軍
專文導讀│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聯合推薦│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仁淵(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徐書磊(法律白話文運動營運長)、顏擇雅(出版人/作家)、王溢嘉(出版人/作家)、吳卡密(舊香居店主)
以版權史為根軸,梳理了關於法律、版權的比較研究、圖書和印刷文化史,甚至擴及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經濟生活等領域。由一門看千門萬戶,也由千門萬戶看一門。王飛仙運用敏感的歷史想像,既能駕馭豐富繁難的史料,又總能在混亂的史事中提出犀利的見解。——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這本書以堅實的史料基礎展現出各方勢力、在不同條件下對版權這個概念的實踐。這些細節重現可讓讀者感受到那個時代,參與出版業的作家、編輯、盜版商、甚至雇用的私家偵探,在一個新開展領域中的來回試探。
——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在作家與出版社的家庭裡成長,使飛仙關注這個議題;而專業的訓練則讓她超越家族,為歷史留下深刻的印記。
——王溢嘉/作家、出版人
一部豐富詳盡的社會史,重建了中國現代史上作者、出版商、國家如何理解版權的意義,展現這些參與者為保護版權而擬訂的策略。智慧財產權和版權是熱門議題,本書架構完整、條理分明,為至今依然爭議不斷的問題提供獨到見解。」──包筠雅(Cynthia Brokaw)/布朗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教授
這部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紮實,檢視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現代中國新興的版權法與版權實踐體系。這部傑作以嶄新角度探討十分重要卻研究不足的課題,對於中國現代史、法律與版權的比較研究、書籍與印刷文化史等領域皆做出寶貴貢獻。──陳利/多倫多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書商、作者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可能是中國智慧財產研究方面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本英文書。傳統見解認為版權與中國文化無法相容,王飛仙透過深入研究和精闢分析顛覆舊說法,展現作者和出版商如何不遺餘力的保護生計。任何對中國資訊經濟感到好奇的讀者都會發現這本書深富啟發性,是不可錯過的好書。──艾德里安.瓊斯(Adrian Johns)/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
《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書商、作者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探詢上海、北京出版界的檔案資料與圈內運作,提供洞見獨到的觀察,深入淺出的介紹中國採納版權的複雜經過。王飛仙不只清楚梳理版權思想在國家長期混亂失序的大環境下經歷何種波折命運,也運用研究發現,以機智巧妙的筆調相當完整的娓娓重述中國現代思想史及文化史。精彩絕倫,讀來引人入勝。──周紹明(Joseph McDermott)/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學士
目錄
推薦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 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推薦序 徐書磊/法律白話文運動營運長
各界推薦
作者序
導讀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緒論
Copyright/版權:外來概念與在地實踐
文化的經濟生活
在國家的陰影之下
第一章 「版權」在東亞的奇妙旅程
讓版權成為「天下公法」
重點在雕版
再譯「Copyright」
從「版権」到「版權」
借用空洞套語再造傳統
第二章 「新學」是門好生意
傳教士的搖錢樹
清末政治改革與新學熱
開拓知識經濟邊疆的捷徑及其亂象
小結
第三章 「著書者永遠之利益」
出售亞當.斯密
將作者的利益合理化
從遠方監控版稅收入
與出版商共享所有權
小結
第四章 介於特權和財產之間
版權特權的浮濫授予
若國家就是盜版者
審視書籍的真正價值
國家喪失身為知識最高權威的地位
將版權和內容審查分離
小結
第五章 棋盤街的「版權」制度
「一盤散沙」
為版權組織公會
建立書籍所有權秩序
在書商法庭懲處盜版商
棋盤街的集體正義
平行共存的「版權」制度
作者應得的收入
小結
第六章 在北平追捕盜版商
上海書商走向全國
新書商面臨的危機
北平:成為盜版之都
經營盜版搜查隊
東安市場書攤和他們的終極武器
盜版商的名譽、偵探的名譽
盜版之王群玉山房
小結
第七章 沒有盜版的世界?
與盜版妥協
自私自利之罪
將作家變成工人
否認個人的才氣
結論
謝辭
參考文獻
試閱
第一章 「版權」在東亞的奇妙旅程
一八九九年春,福建地方文人林紓接到上海維新報人汪康年(一八六○—九一一)提出的奇怪請求,事涉林紓翻譯自小仲馬(Alexandre Dumas)《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此書是他不久前跟友人王壽昌(一八六四—一九二六)合譯完成的,原只是為了打發漫漫冬日的消遣,卻在林王兩人的好友魏瀚(一八五○—一九二九)於福州以雕版刊行後,成為掀起熱潮的暢銷書。汪康年看好此書的潛在商機,熱切表示願意支付優渥酬金,請林紓同意讓他在上海重版此書。這大概是中國史上最早符合現代意義的版權交易之一。
雖然林紓後來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身價最高的西方小說翻譯家,但他在一八九九年婉拒了汪康年提出的條件。他透過共同友人轉告汪,他們翻譯小說不過是自娛娛人,並非為了盈利,因此無意收下這筆錢。他還認為真正有資格「出售」《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權利的人不是他,而是出資促成雕版刊刻的魏瀚。汪康年向魏瀚接洽,魏瀚最終同意「出售」此書,不過他和林紓一樣無意從中獲利,只向汪康年索價木刻雕版的成本費用。儘管知道汪康年打算用西式活字印刷重版此書,魏瀚仍堅持把整套木刻雕版送到上海,以完成這筆交易。
時值中國文化經濟發展的轉捩點。這起事件提供一個獨特的觀察點,讓我們看到,當版權以「西方」概念之姿傳入中國,如何在形塑中國新的知識所有權觀念的同時,也受其原有書籍所有權觀念的影響。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知識界重大的思想轉向,以及清政府的變法改革,使市場上對西學和西方文學作品的需求突然增加。空前巨量的外國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同時,數百甚至數千個新詞彙也應運而生。這些譯介自外國的思想、實踐、制度與事物,往往被視為「新穎」、「文明」、「進步」的體現,值得中國努力效法。而「版權」(copyright)的概念,也是其中之一。
或許我們可把《巴黎茶花女遺事》這耐人尋味的交涉過程,看作一場雞同鴨講的對話:一方熟悉版權的語彙,另一方則不諳此道。汪康年希望獲得的是譯者林紓的授權,他可能認為文學作品的所有權,當然握在創作者手中,該由創作者全權掌控作品如何使用及販售。汪的理解接近今日智慧財產權的意涵,然而他最終得到的卻是一套實實在在的木刻雕版,對他無用武之地。這起事件反映西方思想傳播至中國時,在中心和邊陲接收上可能的時間差。汪康年在通商口岸上海創辦多家維新政治報刊、鼓吹西化,他對西方思想更熟悉,比身在福建的眾人更早受到「啟蒙」。
不過林紓與魏瀚的應對,也顯示版權的概念在引進中國時,在地文人對其意涵並非懵懂無知。林魏兩人或許不瞭解何謂版權,但他們清楚知道書籍所有權是一種可轉讓的私有財產。他們認為印製《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專屬權利及能力,由木刻雕版的出資製作者及持有者獨佔。對他們而言,讓此書得以問世的不是筆耕譯寫,而是那套雕版。因此唯有當這套雕版從福建運到上海後,所有權的交易才算正式完成,即使汪康年打算選用其他印刷方式也無所謂。他們主張,唯有將雕版送給他,方能將印製(及販售)更多冊《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能力,轉移給此書的新所有者汪康年。
因此這並不是版權「內行人」和「文盲」間的困難溝通,而是因雙方對何者體現「有權印製」(right to copy)有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曲折交涉。藉由追溯英文「copyright」如何成為中文「版權」一詞(其字面意義是「版的權利」),本章將檢視東亞早期的版權提倡者與使用者,在這兩種對書籍所有權的不同理解之間,反覆折衝交涉的辛苦掙扎。本章探討早期提倡者關於版權概念的修辭與論述,但提倡者及其同時代人以「版的權利」之名所採取的實踐,才是著者關切的核心主題。東亞的版權提倡先驅,往往將版權描繪成當地文化之前未曾存在過的西方進步普世原則,強調為了國家存亡,必須將版權制度人工移植到國內。然而本章主張:從同時代人實際上如何實踐「版權」的作為,可以看出實情並非如此──許多用來宣告「版權所有」的「新」手段,乃是源自明清或德川晚期書業用來保障印書利益的慣習。
讓版權成為「天下公法」
要追索「版權」這個概念進入中國的旅程,我們必須從日本開始,畢竟中文的「版權」一詞不是在中國誕生的。結合「版/版」跟「権/權」兩個字譯出「版権」(版權)一詞的,是明治時期影響力數一數二的公共知識分子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在日本現代史標準敘事中,他是「文明開化」的主要推手,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般的存在。在一八六○、七○年代,福澤諭吉將各種西方思想和習慣介紹給日本,上至民權、下至食用牛肉,力圖將日本改造成強大而獨立的現代國家。一八九○年代,回首當年,福澤諭吉自豪地將「新日本」的誕生歸功於他對外國思想的譯介。他在自傳中強調創造「版權」一詞的重要性:「當時(日文當中)沒有詞彙可以傳達版權的意涵。沒有人真正瞭解著作出版的專有權歸作者所有,是一種私有財產。」福澤聲稱,自己發明新詞以體現此概念的精髓;此舉不單是將一個英文字彙譯為日文,更是啟蒙國人同胞,讓他們認識一種日本尚未存在的先進財產權概念。
在這番自誇的言論中,福澤諭吉避而不談的,是他將版權引進明治日本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了說服同時代人尊重新的版權原則,實際上他兩次翻譯「copyright」:第一次係一八六八年前後,譯為「藏版の免許」(持有雕版的許可),後又在一八七三年改譯為「版權」。他避而不談的還有另一樁:他之所以熱切提倡版權,不全是出於某種崇高的啟蒙理想,更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計,對抗當時猖獗的翻印者。福澤諭吉前後兩次翻譯「copyright」一詞的那幾年間,正是他出版事業的高峰,也是他最積極採取法律行動處置翻印盜版的時期。因此我們理解在他對版權的翻譯與實踐時,也必須一併考量福澤的經濟生活,尤其是他的「文明開化事業」。
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夕展開其「文明開化事業」。下級武士家族出身的他,先接受傳統儒學教育,後又投身蘭學──蘭學是近代早期日本透過和荷蘭接觸所發展出來的西洋學問體系,尤其著重於科技和醫藥。雖然他的蘭學專長為他在家鄉藩邸贏得正式蘭學教席,但在他發現當時的國際語言是英語而非荷語後,便很快轉而學習英語。為了鍛鍊英語,他在一八六○年自願加入德川幕府首次派往美國的官方使節團,一八六二年又再次參加赴歐使節團。身為極少數有機會親身遊歷西方的日本人,福澤諭吉開始介紹自己在海外見識的「文明國家」,將之描述為日本國家建構的楷模;同時他也希望善用這些海外閱歷增加自己的社會和文化資本。一八六七年,他在隨團赴美出使時,未經許可購入私人圖書回國,導致他在政府的譯員職位被停職,被懲處之後,他便決定辭官自謀生路。福澤諭吉不只開辦家塾──慶應義塾,更將大半精力投入著述,編纂書籍介紹各種西洋事物,希望將海外閱歷化成金錢收入,支持家庭與私塾的開銷。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九年間,德川幕府失勢、天皇權威重振的同時,福澤諭吉也脫胎換骨,從領取俸祿的武士搖身一變成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著書立說維持生計。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治領袖發起全盤西化的改革,以迎頭趕上西方世界,福澤諭吉的著作恰逢其時,為日本讀者提供關於西方社會情況、政治體制、文化規範的簡明介紹。他以西洋權威之姿登場,獲取可觀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成為當時的暢銷作者。不過書籍的成功和名氣,也引來圖利之輩翻印或抄襲他的作品。這嚴重危及了福澤的出版計畫。舉例而言,根據他的估算,《西洋事情》出版兩年內共賣出四千冊左右,但與此同時,至少有三種「偽版」(盜版)共約九千冊,在京都與大阪售出。因此儘管《西洋事情》大獲成功,他仍無法累積足夠資本,出版續作《西洋事情外編》,進一步介紹歐洲法律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思想。福澤向書商朋友抱怨,他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七年間出版的五本書都遭到大量翻印,事業蒙受重創,不得不將出版計畫延後數月之久,甚至一度必須賣掉一本書的雕版以打平開銷。
幾經波折後,《西洋事情外編》終於在一八六八年夏天刊行。讀者在書末可以發現數個章節討論私有財產權與經濟發展的關連。福澤告訴讀者,歐美「先進」國家承認的各種財產權裡,有一種特別的財產權,名為「copyright」,譯作「藏版の免許」,即持有雕版的許可。根據他的闡釋,「藏版の免許」應該理解成法律規定下的作者壟斷權:作者是著作的合法所有者,獨享重製其著作複製品所產生的財產權利益。他進一步說明,綜觀人類歷史,直到晚近,在法律上仍然只有形物體被視為私有財產,但大家逐漸認識到知識也應該視為一種財產。這正是近來歐洲各國詳細立法規範「藏版の免許」的原因;這也表明「藏版の免許」是深受西方世界重視的進步法則。在介紹「藏版の免許」的簡史以及各種度不一的保護時效後,福澤接著強調西方各國對未經授權逕行翻印者的罰則是大同小異的──沒收翻印本、向盜版商收取罰款。
福澤諭吉對版權法的簡介既不創新也不特出,就全書而言也不是特別重要的篇章。重要的是這些內容出現在書中的方式。編纂《西洋事情》和《西洋事情外編》時,他大量援引兩本十九世紀中葉的熱門政治經濟學入門教科書:英國錢伯斯出版公司(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在一八五六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for Use in Schools and for Private Instruction),以及弗朗西斯.韋蘭(Francis Wayland)一八五六年的《政治經濟學要素》(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西洋事情外編》的內容多半是譯自《政治經濟學》,佐以福澤諭吉自由發揮的詮釋,不過《政治經濟學》並未論及版權問題。他在翻譯《政治經濟學》關於私有財產的章節時,為了讓版權合乎論述脈絡,特別插入兩段內容。他先從韋蘭的書中摘錄關於各類勞動的討論,再從《新美利堅百科全書》(The New American Cyclopedia)擷取兩小節關於專利和版權的說明,將之插入《政治經濟學》討論私有財產的篇章。《政治經濟學》主張,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不僅必須保護私有財產,也必須保護私有財產衍生的利益,藉由插入這兩段內容,福澤諭吉將專利和版權融入《政治經濟學》的論點之中。與此同時,在韋蘭討論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脈絡下,福澤諭吉得以將版權定位成腦力勞動的合法報酬。
透過上述編排,福澤諭吉巧妙地在《西洋事情外編》第三卷黏綴出一個關於私有財產權進化的論述,作為其反對未授權翻印的理論基礎﹕人類天生渴望創造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這份渴望塑造了經濟發展的原則和軌跡。相較於蒙昧落後的社會,文明社會的經濟更先進,其定義和保護有形、無形財產的方式因此也更成熟。專利和版權是最晚進納入西方法律保護的財產形式,所以也是最先進的財產形式。西方各國體認到思想、文字創作、發明皆是容易遭到他人「竊取」的無形之財產,因此嚴訂法律,懲罰侵害版權和專利的行為。立法是為了保障人民持續發明、寫作的意願,如此文明方能永續演進,經濟不斷成長。
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確定福澤諭吉是否因為當時遭遇盜版問題,才插入了版權的相關內容,但《西洋事情外編》中關於「藏版の免許」(版權)的敘述,密切呼應他在一八六八年針對未經授權翻印問題所提出的一系列請願和公開聲明。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要素》都沒有直接將私有財產的發展描述成「文明」的進程。創造這種演化論說法的是福澤諭吉,他將文明國家的版權、經濟進步、法律規範三者相互串連,強化他要求版權保護的論理依據。舉例而言,一八六八年春,福澤諭吉在《中外新聞》發表公開聲明,譴責未經同意而翻印其著作的奸商,他指出此種行為是「萬國嚴禁」。同年秋天,在《西洋事情外編》刊行的前後,福澤諭吉向明治新政府呈上措辭有禮但內容大膽的請願書,他指責翻印其書籍的京都書商「行事貪婪,只貪圖一己之利,不顧天下文明之利害。」並說此等行為「不會受到世界上任何開明政府容忍」,若政府若不嚴懲盜版商,日本必遭重視版權的文明諸國所鄙視。
重點在雕版
諷刺的是,這套在明治初期在「文明」之名,受到推崇並實踐的,並不真如福澤諭吉所描述那樣的,是套來自「西方」因而「普世」的法則,而是一些在德川時期日本書業中,行之有年的慣例。儘管福澤諭吉日後宣稱,他為了抓住「copyright」的精髓,而不得不創造新詞,將這個陌生的新概念介紹到日本,但事實並非如此。他的第一次翻譯,不過是把日文原有的「免許」與「藏版」兩個詞語結合在一起,將「copyright」定義為「持有雕版的許可」。固然福澤在其著作和請願書中,強調作者(即著作的創作者)握有使用及販售著作的專有權,但他借用德川時期書業的用語所拼湊出「copyright」的譯名,卻導致其同時代人(甚至福澤本人),在提到「copyright」時,聯想的未必是對無形知識創作的所有權,反而是對有形雕「版」的所有權。
要理解這種誤解是怎麼造成的,我們必須深入探討雕版在德川時期(一六○三年—一八六七年)的文化生產中扮演何種關鍵的角色。此時日本的出版業已經高度商業化,雖然傳統上公家機關或私人出版的書籍,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也可在市場上看到它們被販售流通。而不論商業或非商業出版的書籍,都在相同的印刷文化與技術環境中生產。與明清時期的木刻出版流程十分相似,在德川日本印行書籍的第一步是雇用雕工將文稿製版,由印匠刷印書頁,再由裝幀師把散裝的書頁裝訂成冊。歐洲的活字印刷,在排版完成後,需一次性印製大量冊數,而後將活字拆散,排印其他內容。東亞流行的刻版印刷則截然不同,雕版一旦刻成,印者可依所需數量或客製需求刷印書籍。根據版木的品質和歷年累積的使用程度,雕版可以傳承使用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之久。理論上,如果擁有一本書的雕版,只要墨水和紙張不虞匱乏,就能隨時視需要印書,也能隨心所欲調整印製冊數。與歐洲活字印刷所需投入在印刷機、活字、工人與作坊的資本相較,東亞木刻出版的印刷的成本和技術要求較低,「出書」過程中所需的最大筆開銷,往往是雕製木版的費用。雕版作為一種有形財產,在德川日本或明清中國,被視為家族、官府或書坊可代代相傳的產業。如土地或房屋一樣,雕版可為數人共有之財產,能夠出租、借用,也可作為貸款擔保品,或抵押債務。
因此不難理解,雕版持有者與投資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推動版木所有權的規範與保護。一六九八年,京都和大阪的書商向地方政府請願,要求禁止他人在當地政府管轄範圍內,翻印他們的刊物。十八世紀初,在日本三大書業中心京都、大阪、江戶的書商和出版商,進一步組成名為「本屋仲間」的行會,負責註冊雕版所有權、決定何種書籍可以出版、調解業內糾紛。得到德川當局的正式認可之後,三都「本屋仲間」進一步透過雕版註冊制度,協助政府審查新出書籍;作為回報,政府賦予他們規範與裁定書籍出版合法壟斷權的權威。計畫出版新書的會員,在將新書書稿送行會審查通過後,將獲頒「開版」的許可,意即製作新雕版並以之印刷出版該書的專有權利。這種名為「板株」的專有權,字面意義為「版的股票」,跟實體雕版一樣,是可以轉讓、共有或租借的財產。上述措施看似與十八世紀英國倫敦書業公會的版權制度極為相似,但其保護主體及所有權的生成與認證方式,則迥然不同。
終其十八、十九世紀,書商行會在地方上強力管制「板株」,並在德川當局的支持下仲裁相關糾紛。此類糾紛多半涉及不同類型的翻印,如「重版」(複製雕版)、「偽版」(偽造雕版)或「類版」(複製部分雕版)。雖然公家機關和素人不能加入行會,無法以相同方式註冊保護其利益,但他們與書商一樣認為持有雕版是關鍵所在,也會向地方政府註冊他們的版木所有權。有別於營利的書商,他們以「藏版者」(雕版持有者)的身分自居。如果作者想保有對著作的絕對權利,最簡單的方法將是出資雕製木版並實際持有版木。換言之,作者必須成為其著作的「藏版者」。
這正是福澤諭吉開展出版事業時的情況。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九年間,他的信件和筆記寫滿了雕版刻製和保存的相關細節,詳盡地記錄作為作者與藏版者的福澤諭吉,如何和刻工、印坊與書商交涉往來。一八六七年夏,他延聘刻工至家中為他的《雷銃操法》、《西洋旅案内》、《條約十一國記》雕版。儘管擁有雕版,福澤諭吉並未親自參與印刷、裝幀或行銷,他選擇和專業書商合作,共同「出版」這些書。舉例而言,東京書商和泉屋善兵衛是《雷銃操法》的發行者;一八六七年九月,和泉屋將該書的雕版帶回自家工坊進行印刷。他估算紙張、印刷和裝幀的成本,收取總銷售額的百分之二十做為佣金,作為藏版者的福澤諭吉則享有剩下的淨利。為了確保和泉屋不會低報印刷冊數,福澤採用通稱「留版」的常見技術:在印刷流程中,他將部分雕版留在手上,和泉屋必須到他家,在其監督下印刷那特定的幾頁。如此一來,福澤便能確切知道和泉屋印製的冊數,如果在市面上發現缺頁的書,也能知道和泉屋騙了他。
就選擇合作書商和監督部分印刷流程,作為藏版者的福澤諭吉享有一定自主權,但他不能全盤掌控出版和販售情形。由於負責控制生產成本的是書商合夥人,他無法確定或估算可能的淨利。注意到藏版者在這種合作方式下遭遇的系統性劣勢,他自一八六八年春開始,於自宅建立完整的印刷出版作坊。他雇用常駐雕工、印刷匠、裝幀師,也大量採購紙張以壓低生產成本,只有販售仍依靠書商。當時福澤所製作的雕版,至今仍有部分典藏於他在一八五八年創立的慶應義塾大學。投身出版事業—這個福澤自稱畢生「最大豪賭」的決定,使他得以轉型成為一個文化企業家。他在自傳中誇耀﹕當他的出版活動在一八七三年達到高峰時,年營業額高到連政府大員都會眼紅。此舉確實能讓他全盤掌控自己書籍的印製,但這也表示未授權的翻印將更嚴重地衝擊他的生計,因為現在他不只出錢雕版,更在印刷和紙張上挹注資本。
一八六八年這一整年,福澤諭吉幾乎月月向江戶(東京)和京都的各方主管機關請願,敦請他們懲罰翻印自己著作的人。儘管地方官員通常及時回應福澤的請願書,但讓翻印者受到懲罰仍十分困難;若對方是貴族或有名望的學者,需要面臨的阻礙更是艱鉅。雖然他一再運用版權即文明的論述,向官員施壓,要求他們保護他的利益,但因為日本尚無正式法律承認作者兼藏版者對其書籍出版的壟斷權,案件的進展,往往取決於個別官員的善意和決心。
一八六九年五月,明治政府頒布了《出版條例》,情況為之一變;此為國家首度立法認可,藉由出版書籍而得的「專有利益」應屬於「書籍出版者」所有。就某方面而言,這可視為福澤諭吉文明論的勝利,因為《出版條例》顯然採用了《西洋事情外編》的用詞。然而《出版條例》對於誰是享有「專有利益」的「專利權人」之定義是矛盾的:法規承諾保護出版商的「專有利益」,但保護時效僅限於「著述者」(作者)有生之年。日本的法律學者數十年來不停爭論《出版條例》立意保護的對象,究竟是不是作者。此外,儘管《出版條例》的措辭看似「文明」,執法者卻仍是東京、京都、大阪舊有的書商行會;當時的明治政府能力有限,因此將執法工作外包給這些近世機構的管理者。力有未逮的新國家,和之前的幕府一樣,賦予這些行會特別的法律地位,仰賴他們維持某種社會規範和市場秩序。我們在這個明治新法規中看到的,是承接德川晚期書業慣習的延續性,而非斷裂。
獲悉行會有權仲裁未授權翻印引起的糾紛,福澤諭吉曾向大阪書商行會提出請願,要求他們懲處在大阪盜印《西洋事情》的商家。由於行會不承認作為「業外藏版者」的福澤諭吉是同業,他必須拜託書商朋友代呈訴願。《出版條例》頒布後,為了確保自己的「壟斷利益」能獲得充分保護,一八六九年十一月,福澤諭吉以書商福澤屋的身分,註冊加入東京書商行會。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四年間,在向政府當局請願時,他也多以「地主商」,而非作者的身分自居。在時人眼中,福澤對未授權翻印提起訴訟之所以合情合理,並非因為他是寫作那些書籍的著者,而因為他是刻製並持有雕版的出版商。
將孕育自歐洲活字印刷文化的版權原則引介至日本之際,福澤諭吉無可避免地受其著作所處的刻版印刷生態所制約。將「copyright」譯為「藏版の免許」的同時,福澤及其時人所接受的那些悠久商業慣例及文化常規,也深刻影響了他們如何理解與實踐「copyright」。舉例而言,儘管在各種針對翻印其著作、「竊取其思想果實」之徒的法律行動中,福澤每每強調版權作為一種「無形財產」的獨特性質,其訴訟的最終目標,卻往往是銷毀盜版書的有形雕版,以確保將來只有他本人(作者兼藏版者),才具備印製這些書籍的能力。
推薦序文
中文版序
生為作家與編輯的女兒,我從小在書中生活。出版社與家庭間的界線是模糊的,書架上的書是用來讀的,走廊上用牛皮紙包起來堆好的,則是拿來賣的;寫作是為了心靈的滿足,也是維生的活計。父母的同事朋友,一邊有著高遠的文學想望,一邊也煩惱著諸如「某某什麼時候才要結算我的版稅」,或者「飛去烏魯木齊抓盜版是否值得」之類的問題。雖然我最終沒有繼承家業,而走上歷史學的不歸路,但這個獨特的成長經驗,讓我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出版文化時,格外注重油米柴鹽的日常運作,及它們和知識界、政治局勢、經濟結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本書試圖呈現給讀者的,也是這樣一個世界。
本書最原始的發想,是探索中國雕版出版傳統與外來活字機械印刷,在清末民初的衝撞與調適。「被視為是源自歐洲活字印刷文化的『copyright』,為什麼在中文裡變成了『版權』?跟雕版有什麼關係嗎?」這個問題引起我的好奇,成為了研究的切入點,並引領我進入一段崎嶇而刺激的旅程。
本書橫跨了晚清、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也涉及晚明與盛清,還有幕末和明治日本的發展。我試圖討論一個較長時段(特別是從中國帝國晚期到現代)的延續性與變化,並將東亞內部的跨文化交流與知識概念的全球史連結起來。本書討論概念與思想的引介,卻關注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習慣,由行為而非論述,去重建當時人對特定概念的認識,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我以在當時活躍於新書業中心上海的文人、書商、出版商為研究對象;雖然這些人群聚在棋盤街四馬路這個小小的街區,但他們的足跡與影響遍及橫濱、福建、北京、天津、蘇州、重慶與延安等地。這是段中國思想結構與文化經濟天翻地覆的時代,本書中的人物也不乏是推動這些變化的知識領袖與文壇明星,但讀者將看到他們「平凡人」的一面:煩惱著收入、懷疑出版商的背叛、斤斤計較盜版造成的損失。這個以「人」而非以「法」為中心的取向,使本書得以將這些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和他們以「版權」為名從事的各種活動連結起來,進而思考在正式法律體系與途徑之外,實際存在且生機勃勃的多元、民間的泛法律機制。
這或許不是一本典型的法律史、概念史、或者文化史的著作,但我希望讀者們跟著本書人物的腳步,看他們如何以「版權」之名,在一個知識體系、文化產業結構、政治法律權威都激烈變化而極度不穩定的時代中,彼此合作(有時阻礙),以探索出在新局面中的生存之道。在那些與官員爭執、在實體書上蓋版權印、聘用私家偵探抓盜版、設局逮人、鑽制度漏洞的日常活動中,他們反覆叩問著:「什麼是書?書的價值與獨特性該如何判定?誰有權複製?誰又真的擁有它?」雖然書籍的形式與定義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些問題對今天生產與使用電子書、有聲書、線上小說與漫畫平台、雲端共享的人們,以及制訂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的專家來說,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得知臺灣商務印書館取得本書繁體中文版的翻譯權後,我忐忑而興奮。商務印書館是我從碩士以來長期研究的出版機構,也是建立中國近現代版權機制的重要推手:是它與嚴復等作者建立起一套可長期維持的版稅制度,是它倡議政府訂定中國自己的版權法規,也是它代表書業反對修改對中方有利的版權條約。它是上海書業同業公會的領導人,也是採取強硬手段查緝起訴盜版商的健將。能夠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的中文版,可說是個魔幻而圓滿的發展。本書的面世,特別感謝林紋沛的悉心翻譯,以及臺灣商務印書館張曉蕊總編輯與執行編輯徐鉞的付出。也感謝學友何立行建議了這個吸睛又有趣的中文標題。
NT$442